「游戏化电影」指的是在形式上深受数字游戏影响的当代电影,主要体现在时空设定、情节结构、视觉呈现三个层面。

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9期,第34-42页,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
目录
游戏化电影:数字游戏如何重塑当代电影
文 | 施畅
摘要 「游戏化电影」指的是在形式上深受数字游戏影响的当代电影,主要体现在时空设定、情节结构、视觉呈现三个层面。就时空设定而言,电影角色频繁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操控时间速率乃至重启时间;就情节结构而言,电影提供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关卡,主角需要打怪通关方能获得奖励与升级;就视觉呈现而言,电影采用大量的准交互式镜头(如主观镜头、跟随镜头),令观众更好地代入局内人的角色。
然而,空间的频繁穿梭容易带来真实感的断裂,时间的循环可逆容易导致意义的溃散,情节的关卡化设计容易将角色的欲求窄化为胜利、升级,视觉的准交互式呈现容易触发角色的暴力行为。游戏化电影本质上是游戏经验在电影创作中的投射、移植及内化,尽管它在电影美学层面不乏创新,但我们仍需对此抱有审慎的乐观。
关键词 游戏化电影;影游融合;游戏经验;新媒介电影
数字媒体学者列夫·马诺维奇在他的著作《新媒体的语言》(2001)中坚称,正如电影有电影语言,新媒体亦有一套属于自身的独特逻辑,即新媒体设计师用以组织数据、打造用户体验的一系列惯例。新媒体语言有时还会反过来影响乃至重塑传统媒体的语言。
正如马诺维奇所追问的那样:我们转向基于计算机的媒体,这如何重新定义了静态影像与运动影像的本质?计算机化如何影响了我们文化中的视觉语言?有哪些全新的美学可能性会出现?

诚然,电影艺术早已不复纯粹,电影正与愈来愈多的媒介形态复合、混杂。随着数字游戏(也称电子游戏或视频游戏)的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游戏施加于其他媒介之上的影响。著名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大声疾呼:「数字游戏塑造了当代文化,是时候该认真对待它们了——游戏或许是塑造新世纪美学意识的最为重要的流行艺术。」
不可否认的是,在数字游戏的影响下,晚近以来的电影艺术确实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我们不妨沿着马诺维奇所指明的方向继续追问:游戏转向如何重新定义了影像的本质?游戏化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化中的视觉语言?有哪些全新的美学可能性会浮现?
一、何谓「游戏化电影」
20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世界争霸战》(1982)被视作游戏融入电影的开先河之作。此类早期实践主要基于电影制作者对流行文化的有意征引,以及对特许经营权的流量收割与盈利诉求,而并未有意识地吸收游戏形式与惯例。

世纪之交的《黑客帝国》(1999)通常被视作「电玩一代」的正式登场,对家用电脑及电脑游戏得心应手的一代人开始进入影坛,携带着和以往人们进入影坛时完全不同的媒介基因,给新世纪电影史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端。
新世纪以来,「电影越来越像游戏,游戏越来越像电影」正逐渐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共同感受。美国电影学者罗德维克在《电影的虚拟生命》(2007)一书中曾有慨叹:如今计算机生成的图像逐渐趋向于「摄影」,而许多互动媒体形式则逐渐趋向于「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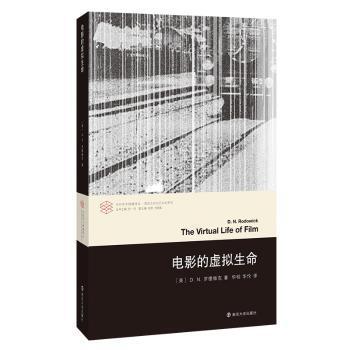
英国电影学者威尔·布鲁克提出了一组对举的概念——游戏化电影与电影化游戏,分别指吸收了游戏惯例的电影和吸收了电影惯例的游戏。不过他本人对这种「媒介联姻」并不看好:「与电子游戏这样一种级别较低的媒介结合,结果就是将电影降低到一个更加没有价值、更加边缘化的境地。它固然赢得了一种新潮时髦的姿态,却全盘舍弃了对严肃艺术的追求。」
晚近以来,针对「游戏化电影」的学术兴趣才逐渐升温。托马斯·埃尔塞瑟与沃伦·巴克兰列举了电影对数字游戏叙事结构的诸多借鉴,其中包括:①程式化的重复动作(积累点数与掌握规则);②多重关卡的历险;③时空传送;④神奇的化身或伪装;⑤即时反馈的奖惩;⑥速度;⑦互动。该分析思路颇有新意,不过失之琐碎,且研究者未能展开充分论述,因此其有效性尚待检验。
也有学者指出游戏化电影可以从「游戏主题」与「游戏形式」两个方面入手展开讨论。前者指的是以游戏为主题及内容的电影,如《黑客帝国》《感官游戏》(1999)等,后者指的是在结构或美学上深受游戏影响的电影,如《罗拉快跑》(1998)、《大象》(2003)等。不过这种「内容—形式」的分类方式也容易遭到批评,毕竟通常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电影在表现游戏内容的同时亦可以采用游戏化的形式。
纽约大学媒体研究者亚历山大·盖洛威在他的著作《游戏化:论算法文化》(2006)中指出,新一代的电影摄制者开始自觉探索将游戏形式融入电影制作,因此研究者们不能再止步于「电影正变得越来越像电子游戏」这一类的陈词滥调,因为这种粗略的描述过度简化了二者日益复杂的关系。为此,盖洛威正式创设「游戏化电影」这一术语,用以指称那些将游戏形式融入电影形式语法的现象。

克罗地亚学者嘉斯米娜·卡洛伊使用与之类似的表述「Gaming Film」,认为游戏文化正在重塑电影的叙事、结构、视觉、哲学等。沿着盖洛威的分析思路,丹麦游戏研究者拉斯·拉森针对可玩的、富有游戏感的新型电影形态,列举游戏化对电影产生的诸种影响,包括游戏世界、游戏化任务、游戏控制器与界面、游戏经验,以及基于玩法的游戏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游戏化电影」区别于「改编自游戏的电影」。前者指的是形式层面的借鉴与融合;后者指的是内容层面的移植与改编,采用更为流行的表述就是「游戏IP的影视化改编」。
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电影评论家让-米歇尔·弗罗东就将「游戏化电影」与「改编」明确区分开来。他将游戏与电影的关系形容为「不纯性」,并将这种复杂关系归纳为评述、改编、引用、结合四种形态:①「评述」指电影可以再现游戏,也可以在再现过程中传递电影创作者的观点和态度;②「改编」指游戏被改编为电影,或者创作者同时推出电影、游戏两个版本;③「引用」指电影对游戏片段的截取和插入;④「结合」指游戏与电影的再媒介化,即电影如何挪用了游戏的形式,或者说游戏如何在形式上融入了电影之中。弗罗东坚称,「结合」(接近本文意义上的「游戏化电影」)才是剖析电影与游戏二者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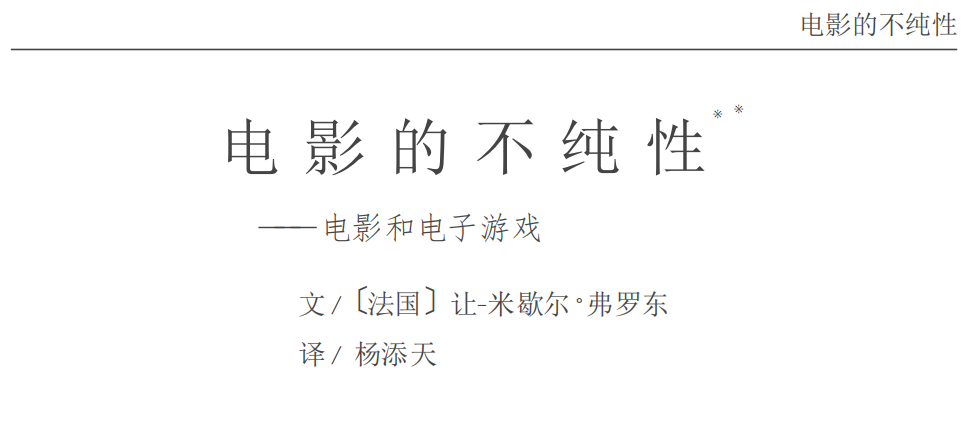
「游戏化电影」近年来也引发了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过他们通常使用的表述是「影游融合」。游戏化电影也被称作「影游融合类电影」,用以探讨电影视觉机制的游戏化改造。
基于「再媒介化」理论的「去媒介化—超媒介化」的分析框架,李雨谏等人指出,影游融合类电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觉经验:一方面,视角拟态以及具有空间导航功能的镜头调度,试图给观众带来一种「在游戏中」的感知体验;另一方面,界面化的画面构成又有意让观众意识到游戏元素的存在,形成一种「在玩游戏」的感知体验。张净雨重点分析了「游戏机制」对影像叙事产生的影响,包括化身操控机制、循环时空建构机制,以及游戏规则机制等。
简言之,所谓「游戏化电影」,指的是游戏形式对当代电影的渗透和影响,重塑包括时空设定、情节结构、视觉呈现等方面在内的电影形态。为此,笔者将「游戏化电影」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时空设定游戏化、情节结构游戏化、视觉呈现游戏化,并在后文中逐一展开论述。

二、时空设定游戏化
游戏化电影的第一种形态是「时空设定游戏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游戏化空间,角色来回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二是游戏化时间,主角可以改变时间流动的速率,乃至加载进度、重启时间。
(一)游戏化空间
游戏化空间的基本设定在于,人物可以通过虚拟化身进入幻境。这一幻想传统可以追溯至美国科幻动作片《电子世界争霸战》。影片主角弗林无意间被吸入一个以计算机电路板为想象原型的程序世界。此后的电影同类设定层出不穷,如《黑客帝国》的母体,《盗梦空间》(2010)的梦境、《源代码》(2011)的源代码世界、《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2017)的尤曼吉热带丛林等。穿梭于虚实之间,好似玩游戏一般,通过登录、加载,玩家可以瞬间置身于某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游戏虚拟空间相当于暂时与外界隔绝的「魔环」,可供角色随时进入,开始游戏。
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反复穿梭于虚实之间,且「撤出/离线」比「接入/上线」难度更大。如果将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解为单次穿行的话——从平常之地穿行到冒险之地再穿行回来,那么游戏化空间的穿行则是频繁的,数量往往不止一次,如《黑客帝国》《源代码》等电影。
不过,穿梭于虚实之间通常需要具备某种物理支持或满足某种限定条件,不可随意穿行,且撤出比接入更为复杂。例如《黑客帝国》,接入母体时脑后插管即可,但撤出母体时则需要接听虚拟世界某处响铃的电话,而反派特工有意抢先一步摧毁之,从而将反叛者永久地困在母体之内。《盗梦空间》的撤出条件是上层梦境或现实中的跌落或溺水,如果过度深入梦境则有可能受困在「迷失域」之中难以返归。「撤出比接入更难」的设定与公众对游戏沉迷的忧虑可谓如出一辙。

更糟糕的是,频繁的穿梭容易造成人物真实感的断裂。人物在虚实之间不断来回跳跃,久而久之往往深陷迷惘,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盗梦空间》通过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向我们发出警告:频繁穿越虚实之间的人物将丧失真切把握周遭环境的能力,原先稳定的地方感犹如手中砂砾一般迅速消散。
然而,即便拥有了判别虚实的能力,人们也未必会毫不迟疑地重新拥抱现实,有时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定的现实。《黑客帝国》向我们抛来了一系列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倘或现实已沦为一片没有阳光的大荒漠,人们是否更乐于选择阳光明媚的虚拟幻境?是忍受贫瘠现实的物资短缺,还是享用鲜嫩多汁的虚拟牛排?我们是否更愿意选择待在虚拟幻境之中,哪怕肉身囚禁在数字培养皿之内?这恐怕是游戏化空间所指向的最为深刻的警世寓言:长久沉溺幻境,幻境已然成为了沉溺者的现实。
(二)游戏化时间
在游戏中,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行调整游戏进程的速度,或加快时间,或减慢时间。减慢时间即让事件的流逝变慢,这意味着玩家拥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玩家操控的化身也就能够在行动速度上超越对头,由此实现克敌制胜、以弱胜强。
这种游戏化的「时间操控」也影响到了部分电影中的时间设定。例如《黑客帝国》中的「子弹时间」就是典型的游戏化时间。尼克与特工史密斯的关系就相当于玩家与非玩家角色(NPC)的关系,二者的反应速度是不一样的:玩家所控制的化身反应速度比NPC对手更快,由此主角不仅可以轻松躲避敌人的攻势,还可以更好地命中、击败敌人。

对于玩家而言,不仅时间流逝的速度是可控的,而且时间还是可逆的。这里的「时间可逆」指的是时间可以循环重启,犹如游戏中的「存档/加载」机制,重复地将角色带入相同的情景。同时,玩家的重复体验也是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即便是一局难度很大的游戏,只要玩家肯不断尝试,最终总能找到破解之道。
以《罗拉快跑》为例,年轻女子罗拉急于帮助她濒临绝望的男友。在影片进行到二十多分钟时,罗拉死于意外射杀,但她并没有接受这个结果,只是睁开眼睛说「不」,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影片开头的场景,犹如重新开始游戏一般。在反复闯关过程中,罗拉逐渐掌握了通关的门道,最终达成了自己较为满意的游戏结局。

《头号玩家》(2018)影片中段,主角韦德在道具商城购买了一块「泽米基斯魔方」,并在危机时刻使用它让时间倒流,从而躲过一劫;影片最后,韦德使用了之前虚拟档案馆馆长赠予的「加命币」,得以在大爆炸之后原地复活。这就相当于游戏被重新加载,角色被「重置」回原先的剧情点,由此满血复活,重新来过。
然而,时间可逆的代价是意义的溃散。反正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人生的意义难免就此滑落,因为原本视作命中注定的那些东西被发现只是偶然而已。《土拨鼠之日》(1993)中,主角菲尔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的无限循环之中。无论他如何选择度过这一天,他都无法再前进一步。惊讶、狂喜、烦闷、焦虑、绝望、倦怠等各种情绪轮流侵占菲尔的感官领域,再也没有稳固、终极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付之阙如。
诚然,「命运之不可回旋」往往是故事中的高度情感时刻,由此故事情节才获得了感人至深的力量。而在游戏化时间中,如果主角可以简单地回过头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么悲剧的动人力量将大打折扣。
因此,游戏化电影中的时间并不是永远可逆的。电影通常会设置时间可逆的条件,倘或条件有变,时间将不再可逆,也即「读档重启」机制的失效。例如《明日边缘》(2014)的主人公只要受伤后流血致死或被输血,就会丧失重启时间的能力。如此一来,战斗便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而可能是性命攸关的背水一战。《源代码》影片的最后,主角主动要求中止现实肉身的存续,随后步入打击暴恐、守护平安的终极一战。在游戏化电影中适当增加不可逆转的剧情片段,可以有效克服由于时间循环重启而造成的意义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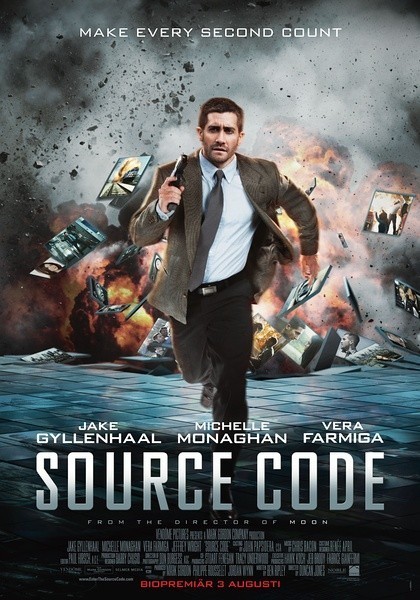
三、情节结构游戏化
游戏化电影的第二种形态是「情节结构游戏化」。在此类电影中,故事情节等同于游戏流程,事情发生的顺序由一系列关卡串联组成,角色依靠武力与智慧逐一闯关,每次通关都意味着收获奖励、提升等级。情节结构的游戏化呈现出三大特点:关卡即情节,闯关即战斗,以及通关即升级。
(一)关卡即情节
故事情节由若干个关卡组成。新的关卡意味着新的空间与新的敌手,也意味着玩家需要寻求新的通关战术。例如《美少女特攻队》(2011)中,每当主角「洋娃娃」跳舞之际,现实场景就会被置换为超现实的游戏场景。主角需要完成以下任务:击败东瀛武士,屠戮奇幻魔龙,勇闯德军司令部,以及大破未来城市。通关之后所获得的地图、打火机、刀、钥匙等奖励,正是主角逃出禁闭空间的关键道具。《盗梦空间》的层层梦境也可以被理解为游戏中的层层关卡。伴随着梦境的深入,闯关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电影叙事通常意味着因果关联的事件,而关卡式情节则未必具备逻辑上的连续性,只是体现为空间或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关系。如此一来,主角的欲望被分解为一连串任务,由易到难,由小到大,每一次任务的完成都是离最终欲望的实现更进一步。
不过,关卡式情节有时难免会为了设置任务而设置任务,主人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脱离主线,从而造成剧情的跳脱感。这也正是评论者所批评的游戏设计中常见的偏向——「主线演进」让位于「空间探索」。换言之,英雄一路游历,所触发的被嵌入旅途的若干小故事实际上无关宏旨。这些小故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设置关卡以锻炼英雄,令其获得宝物、提升段位。
(二)闯关即战斗
闯关在游戏中通常意味着频繁的战斗,而游戏化电影区别于冒险动作电影的地方在于它更倾向于以游戏化风格处理战斗场景。例如《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2010)的主角斯科特为了赢得梦中情人的芳心,必须接受女孩的七位邪恶前男友的挑战。
每一次战斗都依据街机游戏《街头霸王》的对战模式来设定,银幕上会出现生命值、绝招、道具、围观者等「街霸式」元素。电影还使用一系列特技、特效(光束、冲击波等)来展示回合制的打斗过程。战斗结束后,观众会听到系统喊出「KO」的声音,失败者变成一堆金币,成功者则获得奖励,顺利晋级。

这种对格斗场景的游戏化呈现,接近于大卫·波德维尔所谓的「装饰性风格」,其功能是在感官上凸显游戏的媒介特征。区别于指示性、主题性、表现性等功能,装饰性的游戏化风格凭借其媒介本性引人注目。
「闯关即战斗」将电影场景变成了一场场眼花缭乱的打斗游戏,更准确地说,战斗基本上成为了解决矛盾纷争的唯一途径。电影中常见的故事通常会从一个充满欲望的人物开始,他/她努力克服成功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而在以关卡式情节为特征的游戏化电影中,关卡成为了冲突的单一来源,关卡的克服意味着期待的满足,主角所要思考的无非是如何克敌制胜。
关卡式情节软化了叙事的因果关联,也牺牲了角色的心理描述。除了数值意义上的经验提升和技能增长,频繁的战斗并不会给主角在心理上带来过多的改变,这也使得主角缺乏性格意义上的成长性。
(三)通关即升级
情节结构游戏化意味着频繁的闯关战斗与通关升级。游戏总会给予通关的胜利者一定的奖励,包括得分、成就、荣耀、战利品、纪念品、强化道具等。奖励会带来武器装备的改良或角色段位的提升。例如《头号玩家》中,通关意味着金币奖励,主角借此购买强化道具用以提升自身的属性或获得额外的技能。唯有不断升级,方能应对接下来难度更高的关卡。不断提升,遇强则强,这实质上构成了游戏设计理念中所谓的「心流」体验。
顺利通关的唯一保障就是不断地增强属性、提升等级。「唯有升级方能克敌制胜」,这一逻辑无疑强化了等级秩序的法则,并将「升级」升格为虚拟世界的统摄性法则,成为了颠扑不破的强力信条。对于故事主角而言,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等级,才能更好地闯关,也才能延续剧情。
这一逻辑在以《斗罗大陆》《凡人修仙传》等为代表的当代玄幻类影视剧中尤其突出。此类影视剧主人公的终极目标多为「逆天改命」成为人上人的强者。「升级」被天然地设定为主角的根本动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就是不停地闯关战斗。

四、视觉呈现游戏化
游戏化电影的第三种形态是「视觉呈现游戏化」。游戏的核心特质在于「交互」,不过在游戏化电影的观影过程中并不存在交互操作,因此笔者使用「准交互式镜头」一词来概括游戏化电影的视觉呈现方式。顾名思义,准交互式镜头并非提供真正的交互操作,而是提供某种交互的感觉。准交互式镜头将游戏的视觉机制移植到电影之中,将观影者变成了「持续观看、不断移动的局内人」,为观影者提供了一种「正在玩游戏」的感觉。
「准交互式镜头」可分为「主观镜头」和「跟随镜头」两种,分别对应游戏中常用的第一人称射击视角(FPS)和第三人称射击视角(TPS)。前者相当于第一人称视角,后者则介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二者均受限于局内人的主观视觉经验。
(一)主观镜头
主观镜头(POV)即第一人称视角镜头,意味着观影者代入了角色的眼睛,镜头里通常只能看到自己的手或手持之物(如武器)。游戏化的主观镜头通常应用于科幻、动作等类型电影。例如,科幻动作片《毁灭战士》(2005)用五分钟的主观镜头来展现被基因改良后的特种兵约翰与怪兽近距离战斗的火爆场景:约翰的反应速度与敏捷度大幅提升,一改之前「被虐」的糟糕处境,犹如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一般痛快淋漓地射杀怪物。

科幻动作片《硬核亨利》(2015)的风格则更为激进,全片以主角亨利的主观镜头一以贯之。被改造为赛博格身体的亨利在追查线索的同时不断被对头追杀,因此影片充斥着大量的激情跑酷、近战肉搏、混乱枪战等场面。主观镜头让观影者好似体验了一场过山车之旅,其剧烈抖动、画面变形不免让观影者感到眩晕、疲惫及恶心,影片也因此惨遭诟病。

主观镜头还可以与游戏界面融合,成为视野与界面融合的「视界」。这种呈现方式与游戏的HUD界面颇为类似。游戏HUD界面将仪表信息以字符或图形的方式予以显示,投射在观看者的视野之内,包括道具、地图、生命值、瞄准镜、弹药量、情境提示等信息。
科幻片《末日重启》(2017)中,主角所植入的视界系统可以记录任务日志,导航行进路线,查看历史影像,识别人员身份,评估物品损坏程度,以及提示医疗健康警告。作为「视界」的主观镜头将被观看对象转化为一连串的属性和数值,也为用户提供针对当前情境的关键性提示,这与游戏化设计的视觉机制相合。

(二)跟随镜头
跟随镜头通常指在人物身后伴随人物行走、不断前进的镜头。科幻灾难片《人类之子》(2006)采用手持跟拍的方式追随主角西奥跌跌撞撞地穿梭于炮火连天的战场。战争片《1917》(2019)更是将跟随镜头发挥到极致,以「伪一镜到底」营造持续的沉浸感。摄像机追随角色持续穿越战壕、农场、废墟、河流、树林等多个场景。不过它并未全程跟在主角身后,而是一直在调整位置,有时在主角前面引领他前进,有时在后面跟随他向前,有时又在侧面伴随他移动。当角色跑动,摄影机也跑动起来;当角色蹲下,摄影机也随之蹲下。

这种视角较为接近《古墓丽影》等当代动作冒险类游戏的第三人称视角,游戏中的摄像机视点通常在游戏人物后方偏上的位置略微俯视,玩家借此可以看到自己化身的全身或半身。与此同时,镜头也不会一味地以固定的角度机械地跟随人物,而是以人物为中心适度调整角度,灵活地展现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联。

如果说战争片中的跟随镜头模拟了战争游戏中紧张刺激的「突围」情境,那么由格斯·范·桑特执导的《大象》中的跟随镜头则模拟了游戏的「漫游」状态。这部灵感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的影片大量使用在纵横交错的走廊中无休止漫步的跟随镜头。导演采用长镜头和手提跟拍的方式,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枪击事件发生当天的零碎生活。镜头跟随着不同的人物,过道、餐厅、活动室、图书室,从此到彼,移动游走。但该片的跟随镜头又与游戏有所差异。影片的机位整体而言是平视的,角色要么是半身,要么是全身,总是填满屏幕,让人倍感压抑。

跟随镜头的一大特点是它令我们无法轻易观察到人物的面部表情,故而无法了解他/她的内心世界。随着摄像机的前进,视野被牢固地束缚于特定人物的背影之上,观影者无从获知人物的面部表情、心理状态及内在动机,从根本上抑制了摄像机对人物内心的洞察。由阿兰·克拉克执导的同名电影《大象》(1989),跟随镜头同样被用来再现人类的暴行。

有论者将跟随镜头的内在美学称作「矢动美学」,其体现为不停向前的运动与毫无思想的行动者,人物的情感、动机、意志均被隐藏、被消除。同时,叙事性要素被压缩至最低限度,影像引领观众同角色一道走向最终的致命冲突。诚如法国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所言,「跟随镜头是一个道德问题」。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准交互式镜头为何容易引发潜在的暴力。英国电影评论家大卫·汤普森指出,游戏化视野并不必然带来积极向上的媒体融合,也可能会导向没有节制且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究其原因在于:
首先,准交互式镜头的观看者总是心痒难耐,总要做点什么,哪怕干点破坏。倘或主观镜头长时间静止不动,其枯燥乏味会叫人难以忍受;跟随镜头亦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象》中漫长的跟随镜头确实令人倍感乏味,直到最后它将观众引向致命的冲突,影片才有了冲击力和震撼力。
其次,准交互镜头是令人不安的镜头。主观镜头的观看者始终看不到身后,故而容易陷入不安、警惕、防备的情绪状态。基于生存游戏的惯性思维,没有人愿意身无长物、两手空空,总是巴不得主角赶紧搜寻武器装备,以便应对随时可能逼近的威胁。跟随镜头的视野也同样受限,观察范围受制于角色的移动,缺乏对局势的有力掌控。
最后,准交互式镜头是匿名的。观影者通过主观镜头无法看到自身形象,通过跟随镜头也只能看到人物背影而已,如此一来观影者/行动者便拥有了匿名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诉诸暴力时的负罪感。
结语
如今电影正遭受着新式媒介的侵蚀,正如早年间传统精英艺术遭受电影的侵蚀一样。与其说是电影遭受游戏的侵蚀,倒不如说是新媒体语言开始施展威力,重塑传统的影视语言。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热衷于讨论媒介之间的整合与协作,更应该看到媒介内部发生的融合。
杨鹏鑫将那些吸纳了新式媒介美学原则、惯例、风格的电影形态称作「新媒介电影」,即以电子屏幕、电子游戏、数据库、录像等新媒介为表现对象,并依靠其进行叙事和影像建构的电影,包括屏幕电影、数据库电影、电子游戏媒介电影、录像媒介电影等。
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电影不仅包括对「材质」的挪用与混合,而且也包括对「形式」的迁移与借鉴。笔者认为,新媒介电影可以适当拓宽其内涵。以游戏化电影为例,它未必直接引用游戏画面和游戏片段,却能够征引游戏元素融入电影形态之中,且这种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电影形态与美学原则的变迁。电影的游戏化进程,本质上是游戏经验向电影或隐或显地投射、迁移、内化的过程。
游戏化电影打破了电影的常规形态与惯例,不乏创新之处,但同时也有窄化的危险。
就空间而言,频繁穿梭造成了真实感的断裂;就时间而言,时间的可逆转导致了意义的溃散;就结构而言,打怪升级主导了情节的推进,角色的欲望被置换为单一的升级与胜利;就视角而言,准交互式镜头难免导向暴力行为。游戏化电影对关卡式情节、准交互式镜头的大批量使用,似乎也能解释为何当代电影中越来越多的暴力打斗与射击杀戮。因此,我们为游戏化电影所带来的美学创新欢欣鼓舞之际,更需要多一份审慎的乐观与严肃的批判。

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9期,第34-42页,责任编辑 方兆力。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