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隔离,方为正义。

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第109-121页,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8年第8期全文转载
目录
内容摘要
20 世纪以来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其空间政治在于隔离与混杂的对立和交锋。按照空间形态,未来城市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垂直城市、极权城市、堡垒城市,以及虚拟城市。
隔离空间意味着阻隔视听,限制流动,拒绝分享空间的功能。隔离主义的逻辑是现代性的逻辑,因重重危机而势在必行。隔离主义合乎理性,也颇有效率,却并非道德,因为隔离空间难免妨害自由。
混杂的力量不容小觑,混杂不仅意味着自由,而且是遏制隔离空间扩张的最后希望,它提醒空间统治者所有的秩序可能猝然消失。「混杂势力对抗隔离空间」的「未来叙事」体现了西方科幻电影的激进政治传统。
关键词
未来城市 空间政治 科幻电影 敌托邦 激进政治
隔离与混杂: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空间
文 | 施畅
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在《技术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一个例子——位于纽约长岛的跨越景观大道的桥梁。这些桥梁被有意设计成较为低矮的,以至于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无法通过。
于是,平常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贫民和黑人就被拦在了外面,而拥有汽车的白人却能够利用景观大道自由地消遣和通勤。
桥梁建筑看似中立,事实上正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影响,这反映出设计者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温纳提醒我们,包括人造空间在内的技术物本身「固有」其政治性:
空间对人们施加的影响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相联系。


有关于空间政治的讨论,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性的,既为权力关系所生产,又生产了新的权力关系。
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
空间景观之所以看似是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是因为占有已然完成,昔日激烈斗争的种种痕迹已被抹去。空间既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同时又有着强烈而主动的生产性。
列斐伏尔更关心「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换言之,空间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也同样支撑并维系了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


那么,未来城市的想象空间是否也具有其政治性呢?
未来城市看似虚无缥缈,实则有其现实依据。未来城市通常被视为愉悦视觉的惊异之物,而维维安•索布切克强调,未来城市的描绘看似抽离历史、超然现实,实则是我们日常经验的想象之物。
詹明信坚称,表面上科幻是对未来的特殊设定,但其实科幻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
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科幻电影的时间通常设定为未来三四十年。约翰•戈尔德认为设定成「近未来」的好处在于「不短不长」:变革的发生似乎可信,又不至于完全无法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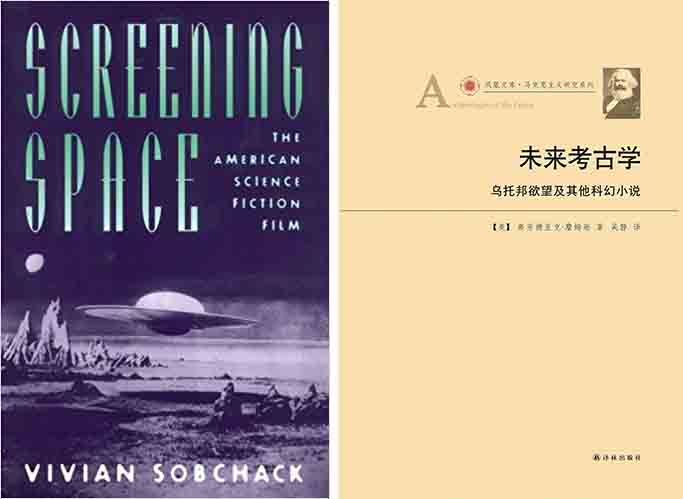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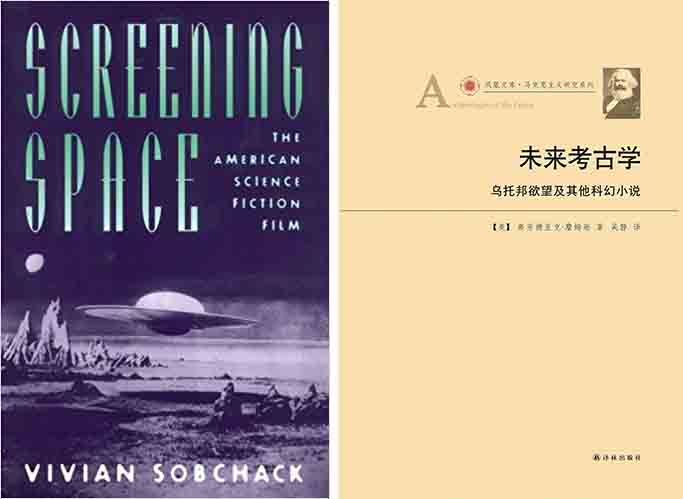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空间并非只是静默无言的背景,而是试图介入叙事。未来城市是一个行动主体,与人物一样可以展开行动,甚至决定故事的最终走向。
索布切克指出,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是一种介入性力量,绝非袖手旁观,而是施加影响。在加里•沃尔夫看来,未来城市所施加的影响固有其倾向性:
未来城市是人类探索未知的障碍物,扼杀好奇,缺乏趣味,尽是已知之物,罕有未知之物。
简尼特•斯泰格则将当代幻想城市的再现风格称之为「黑色未来」,其特征包括:后现代风格、间接打光、错综复杂的空间,以及趋于混乱的文明。
本文将主要考察以电影为主的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关心其空间构型以及政治面向。
未来城市的空间设计通常被认作奇思妙想,但我并不会急于将其宣称为不可思议,而是将它们纳入历史的语境予以辨认,并试图建立未来城市演进的历史脉络。
列斐伏尔的提醒是有益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如果纯粹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空间,空间就会被降为一种仅供阅读的信息或文本,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历史和现状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城市的空间变迁并不总以断裂的方式出现,而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来而复往的演进方式,因而历史分期并非绝对,或有重叠之处。这也意味着旧的城市形态在新的阶段仍有可能继续存在。
我们将看到,未来城市面临重重危机,隔离空间应运而生,试图对整座城市施加影响。不过隔离并非无往不利,混杂之地是隔离鞭长莫及的地方。在那里,混杂势力不受驯服,随时准备进犯,企图挑战未来城市的隔离秩序。
一、未来城市演化史
首先,我们有必要追溯乌托邦的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乌托邦并非未来世界,而是藏匿在世界某一角落、有待发现的异域空间。乌托邦的作者大多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不甚满意,因而乌托邦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旨在构想人类社会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不妨将乌托邦视为乌托邦作者理想中的未来城市。
有关乌托邦的叙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小说中一位航海家向我们透露了这座孤悬海外的城市的种种信息:城市建筑无不巨大壮丽,布局相仿,外观无甚差别,人人自由进出。
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装的是折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事实上,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乌托邦」的最大特点是消灭私有、财产公有,因而城市中的任何空间归公共所有而非私人独享。


《乌托邦》的创作动机通常被认为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密切相关。面对沉重的现实,莫尔试图一举消灭圈地运动所制造的隔离。
在莫尔以及马克思的叙述中,圈地运动均暴虐异常。马克思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暴力赶出自己的家园,许多人沦为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莫尔同样看到了圈地运动的黑暗一面,因而他在《乌托邦》中激愤地痛斥:
绵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尽管圈地运动并不都是暴力的,但土地的集中意味着原本持有土地的农民们将不得不离开乡村,另谋出路。
旨在消灭私有产权所带来的隔离的乌托邦,同时也是在制造新的隔离——清一色的公共空间也许并非幸事。大卫•哈维对乌托邦有过批判:
莫尔为了和谐稳定,不惜将任何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排除在外;乌托邦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乌托邦的空间服务于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过程,「真正的历史」被排除在外了。
乌托邦的城市空间,布局异常有序,建筑高度同质,出入毫无限制,以此实现绝对的平等。看似自由的乌托邦,实则已经埋下了隔离的祸根——将个人与私人空间彻底隔离。私有制被消灭,私人空间绝迹,乌托邦并不打算为异质性的力量提供容身之所。
张德明对《乌托邦》《新大西岛》《大洋国》三个典型的乌托邦城市空间做了概括:
乌托邦外部空间的特征是与世隔绝性和不可接近性,而其内部空间结构则表现为自我复制性和普遍类同性。
乌托邦的最大悖论在于:意在消灭隔离的美好愿望,蜕变为制造隔离的禁闭力量。


(一)垂直城市:大机器和摩天楼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未来城市,其空间形态可以概括为「垂直城市」,大机器和摩天楼是垂直城市的显著特征。
两次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环境,其典型就是狄更斯《艰难时世》(1854)中的「焦炭城」:
工厂蜂起,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烟尘滚滚。
在当时不少人看来,蒸汽机的噪音是动力和效率的标志,烟囱的烟尘是繁荣的象征。城市当然在进步,但代价高昂,机器正逐渐显示出暴虐的一面。1908 年,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面对日益被工厂侵占的英格兰土地,不由感慨道:
满目皆是无情工作的机器,车轮飞转,齿轮暴虐相迫,此非伊甸美景。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与内燃机作为标志,由此带来的集中化和巨型化趋势让一座座巨型城市拔地而起。据约翰•戈尔德的观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未来城市多为垂直而起的巨型城市,充斥着邪恶与压迫的力量。
基于当时英国欣欣向荣的采矿、冶金产业,威尔斯认定未来工业将从地上往地下迁移。在未来,地上将是富人的享乐之地,而地下则是劳工的受难之所。
在威尔斯小说《时间机器》(1895)中,未来人类将进化为两类:艾洛伊和莫洛克。前者生活在地面,体质柔弱,好吃懒做,智力、体能都严重退化。后者生活在地下,粗暴蛮狠,长得活像猴子。莫洛克负责供养艾洛伊,而艾洛伊一旦成年则将沦为莫洛克的盘中餐。两个种族分别影射了资本家与无产者,其冲突很容易被解读为阶级暴力。


电影《阿高尔:权力的悲剧》(1920)中,主人公意外获得了一台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电力的机器,进而从贫苦劳工一跃成为大资本家。尽管新机器让矿工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人们发现自己又被重新置于电力垄断的剥削之下。


崛起在望的垂直城市,不仅基于对工业城市的初步判断,也合乎城市规划者的设计蓝图——对传统城市加以现代化改造在 20 世纪初是大势所向。
意大利建筑学家圣伊里亚认为,现代城市应该从机械世界而非自然或传统中找寻灵感,他宣称「钢骨水泥所创造的新的美,被徒有其表的骗人的装饰玷污」。法国建筑学家勒•柯布西耶给出的方案是高层建筑和立体交叉,希望增加人口密度的同时减少市中心的拥堵。



两年之后,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的理念在电影《大都会》(1927)中得以落实。1924 年,德国导演弗里茨•朗出访美国。当他乘着蒸汽船抵达纽约港之际,曼哈顿的天际线让他大感震惊。次年弗里茨•朗便开始着手拍摄《大都会》。
「大都会」堪称未来城市的经典模板:摩天大楼令人眩晕,立体交通复杂而有序。只有少数精英有幸生活在华丽的高层建筑之上,享受优渥的生活。
对于广大劳工阶层而言,大都会是一座绝望而恐怖的现代工业城市。为了维系城市的日常运作,机器日夜轰鸣,如同咆哮的怪兽,工人们挥汗如雨,濒临枯竭。


不同的阶级之间被一道道坚硬的闸门隔离开来,不允许有任何的接触,以此保证每个阶级都能够各居其位、各安其命。宏伟建筑往往掩盖了阴暗角落的污泥浊水,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对身处幽暗地下的同胞们的悲惨命运一无所知。
不过,严酷的隔离并不能阻止混乱的降临。最终,混杂的力量肆意冲撞,引发洪水泛滥,「大都会」岌岌可危。


垂直城市更加深刻的隔离在于刘易斯•芒福德所谓的「机械文明」即机器体系给人们施加的某种机制或者说秩序——统一性、标准化、可替换性。
工厂是禁闭的,倒不是说工厂不允许你离开,而是你无法离开工厂,因为劳动力和劳动技能分离了——离开了机器,工人已经不会干活了。
倘或不甘心沦落为一个「齿轮」,劳工仅剩的反抗或许就是《摩登时代》(1936)中卓别林式的胡搅蛮缠、制造混乱了。
破坏秩序的混杂力量往往很难见容于城市,爬上帝国大厦之巅的「金刚」(1933)不啻一个「混杂势力冒犯隔离城市」的隐喻:胆敢挣脱锁链的野蛮生物,必将在战斗机的扫射下轰然坠地。


垂直城市不一定就建在地表之上,也可以建在地下。改编自威尔斯 1933 年同名小说的电影《笃定发生》(1936)讲述了一个故事:人类社会在世界大战之后堕入莽荒,瘟疫蔓延,军阀混战;最后靠着先进技术,人类文明才得以在地下重建。普罗大众更倾向于保守,认为探索太空是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而少数人则意识到抱残守缺并非长久之计,最后他们冲出重围,毅然向广袤无垠的宇宙进军。


(二)极权城市:电幕和管道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未来城市,其空间形态可以概括为「极权城市」,从中不难看出冷战、核战威胁的诸多痕迹。
极权城市的隔离空间是一股不断进取的排斥性力量:隔离肆意扩张,试图清除一切混杂因素,消灭一切反抗势力,从而保证空间的绝对纯净。
电幕和管道是极权城市的两个重要的空间装置。电幕的无处不在意味着监控无处不在,管道的无尽延伸意味着官僚制度的无尽渗透。
乔治•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1949)中的未来城市到处是电幕,城市空间被置于监视之下,人们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控之中。时刻运转的国家机器,用宣传把人们和糟糕的现实隔离,用修订把人们和断裂的历史隔离,用禁欲把人们和情爱隔离……
极权政治永远宣称集体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藉此掩盖个体正忍受贫瘠的现实。你无法奢望更多的东西,只有无尽的墙和无数的铁幕。侥幸的是,私人日记、郊外树林是溢出隔离之外的秘密小道。
然而,监控和隔离最终还是侵蚀了混杂空间,主人公的命运急转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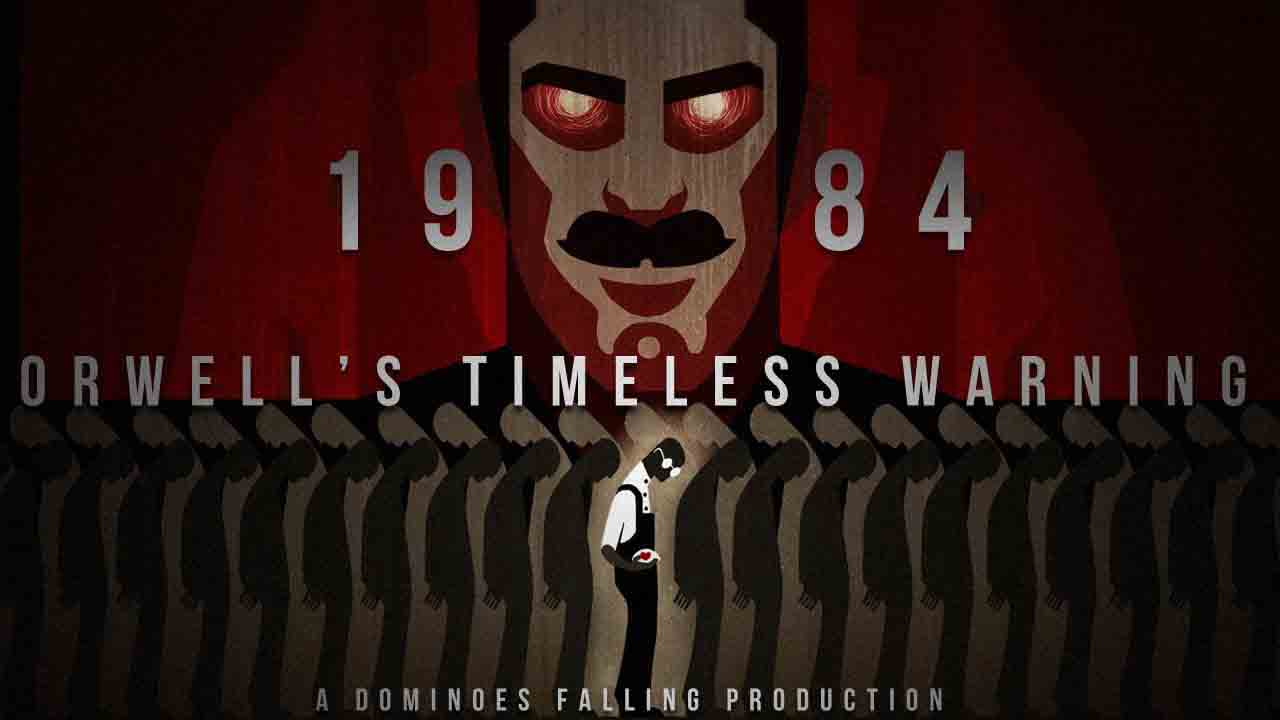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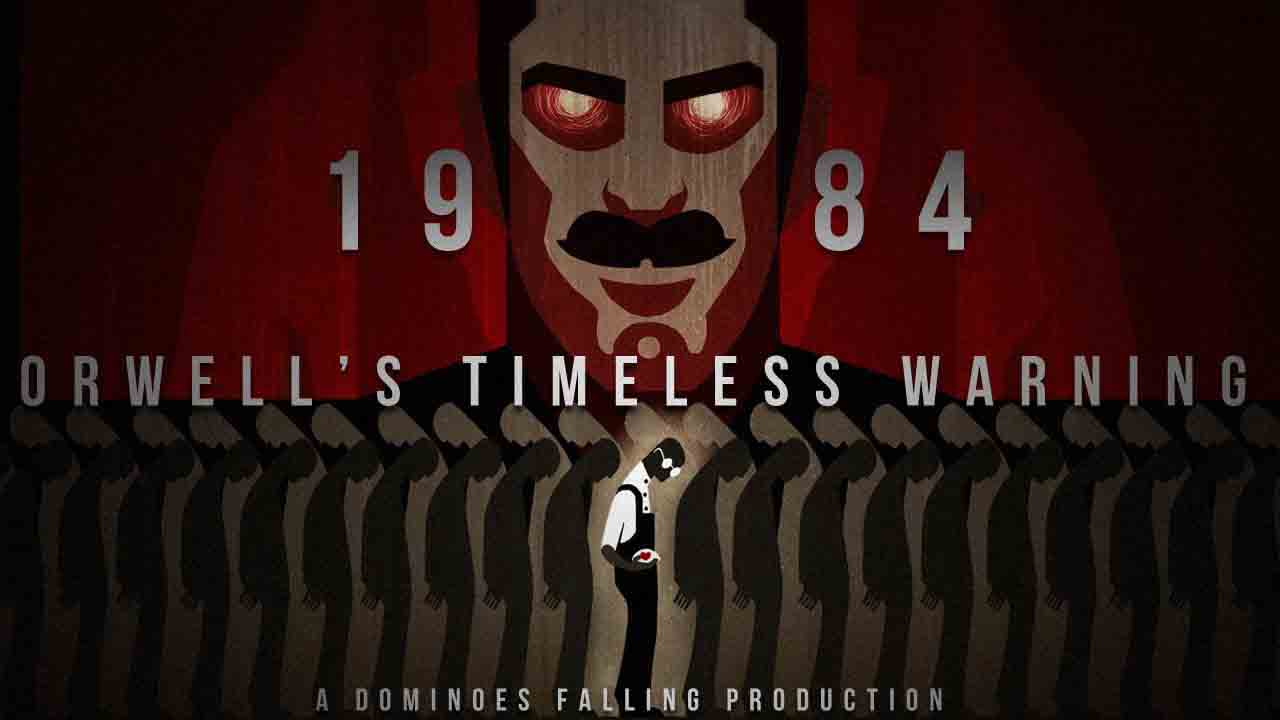
电幕只是监视装置的一种,极权城市当然可以另换一套装置,但其实质不会改变:视觉霸凌空间,逃逸毫无指望。
让-吕克•戈达尔编剧并执导的电影《阿尔法城》(1965)描绘了一座死寂冰冷的未来都市:城市被置于一台名为「阿尔法 60」超级计算机的统治之下,一切都必须遵循其绝对理性的逻辑,违反者即刻被枪决。
在特吕弗的电影《华氏 451 度》(1966)中,未来城市禁止读书,所有书籍都要收缴并焚毁(华氏 451 度正是纸的燃点)。消防员的任务不是灭火救人,而是焚书和抓捕读书人。爱书者只好遁入茫茫荒野,把书背熟以便日后流传。
卢卡斯的电影《500 年后》(1971)将未来城市设定为地下,白色的建筑,白色的制服,别无他物,唯有荒凉。冰冷的监视器时刻运行,人们被迫服用药物,从事繁重的集体劳动。


管道是官僚系统的绝妙隐喻,一方面保证了权力意图的高效落实,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可变通而导致各行其是的后果。
小说《一九八四》中,体制的运行严重依赖管道:上级指令即刻传达,下级则被要求立即回应和迅速落实,不容半点拖沓。
电影《妙想天开》(1985)则呈现了「管道空间」另一个极端:凡事需填表,照章才办事,不可变通,各行其是。在电影中,管道已经实现了对未来城市的全方位渗透。倘或哪条管道出错,其后果不啻一场灾难——繁琐拖沓的审批程序并不解决问题,反倒雪上加霜。


与管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街道是自由自在的,难以监控的。马歇尔•伯曼曾谈到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道,认为街道是政治事件的发生之地,政治力量由此展开,政府难以监控。阿兰•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1993)中也强调,公共街道是一个特别的政治空间,是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交汇之处,能够表达出人们最珍贵的理想,也最难以掌控。
尽管街道也难免会受到监视,不过管道受到的监控更甚。走在街道上,你可以回头确认有无跟踪的便衣,抬头确认有无监控的摄像头。然而管道却无从确认监控的有无,或许管道永远处于监控之中。在极权城市,街道不可避免地衰落,而管道则无穷延伸进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三)堡垒城市:构筑围墙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未来城市,其空间形态可以称之为「堡垒城市」或「防御空间」(Oscar Newman 语),以「构筑围墙」为特征,以确保安全为宗旨。
和极权城市一样,堡垒城市也害怕混杂势力,但他们的做法并非不断进取,而是划地为限、关门大吉。堡垒城市的隔离空间,旨在防止混杂溢入堡垒城市,具有退守防御的性质。
大卫•哈维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了,开始重建特权精英阶级的力量,同时也加速了城市的分裂:这头是富人的伊甸园,另一头是穷人的贫民窟,城市分解为一个个或穷或富的微型国家。在此背景下,以安全为目的、以防御为手段的隔离空间颇受青睐,堡垒城市应运而生。
1980 年代前后的纽约市令人望而生畏,暴力犹如病菌一般进入城市的血管并周流全身。想要不受侵扰、稳稳当当地穿过中央公园或是沿河行走,竟已成了奢望。芒福德无比沮丧地承认,秩序与法律都拿当时的纽约没有办法。威廉•吉布森回想起当年的曼哈顿:
满目疮痍,多数房屋人去楼空,夜晚人们为了安全而燃起的篝火能照亮夜空。


原来住在市中心的白人纷纷逃离内城,迁往郊区,而越来越多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则滞留在中心城区。人们如果无法征服城市,至少可以逃离城市。芒福德把迁往郊区看作是中产阶级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抗议。郊区化是中产阶级的大撤退,退入隐蔽地带,从空间和阶层上与其所认定的危险势力隔离开来。
电影《纽约大逃亡》(1981)讲述了纽约城被废弃的命运:1988 年,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犯罪率,联邦政府干脆将曼哈顿岛改建成一座庞大的监狱,囚犯们被扔到里面自生自灭。纽约城变成了犯罪之城,任由混杂势力盘踞独大。


内城的衰落,在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也有所体现。詹明信把它称作「肮脏的现实主义」,认为传统的共同体城市就此终结。未来洛杉矶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整座城市深陷黑夜,似乎从来没见过阳光,到处燃烧着火球,烟雾弥漫不去。高楼林立密布,交通拥堵不堪,酸雨下个不停,垃圾遍地都是,霓虹闪烁,终日泥泞。随意挑一条幽僻的小道走走,便可通往某处藏污纳垢的地方。


一群仿生人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从他们的服役之地逃到地球,希望可以找到延续生命的方法。仿生人选择藏身于都市的混杂空间,并闯入制造仿生人的公司总部寻找真相。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银翼杀手的追杀——或许可以将其视作对隔离空间的破坏者的彻底清除。


面对混杂势力的入侵,隔离空间趁势崛起。公共空间被私有化逐渐蚕食,转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隔离空间。莎朗•佐金描述了 1980 年代的曼哈顿商业区如何通过对流浪者的驱逐来实现自身的权力景观,毕竟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不免会叫光鲜亮丽的商业区难堪。这不啻反映出一个现实:公共空间不再无条件地向公众开放了。
迈克•戴维斯在《水晶之城》(1990)一书中对洛杉矶城的观察尤为深刻:八九十年代,洛杉矶的城市空间对待穷人极不友善,当权者故意制造一种不舒适、不便利、硬邦邦的空间效果以达到隔离的目的。城市空间的执法者针对流浪者定期扫荡、反复驱逐。而富人们则退入戒备森严的「堡垒」中严阵以待:雇佣武装安保,给大门上重锁,安装监控摄像头,等等。戴维斯将其称之为「街头冷战」。
戴维斯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两年之后「街头冷战」转为「热战」。洛杉矶发生举世震惊的大暴动,种族之间爆发激烈冲突,造成严重的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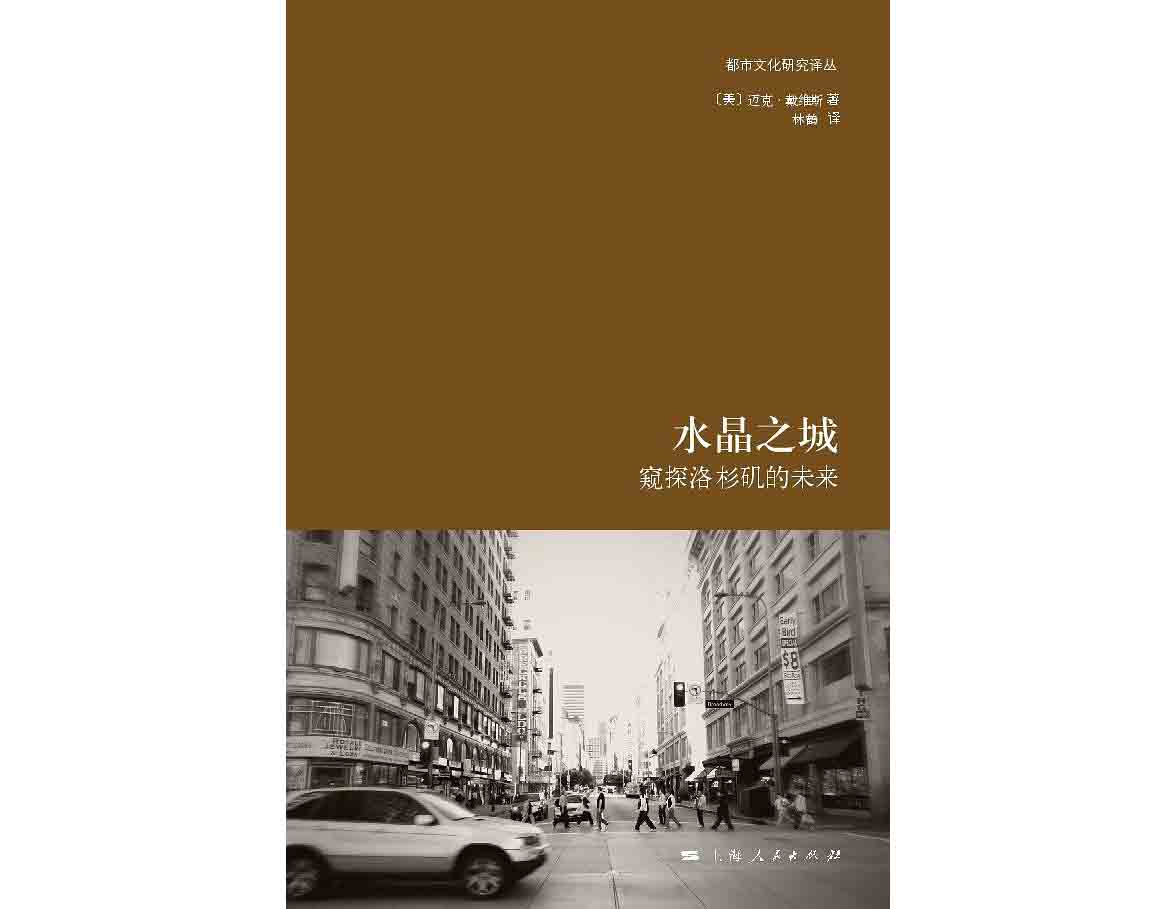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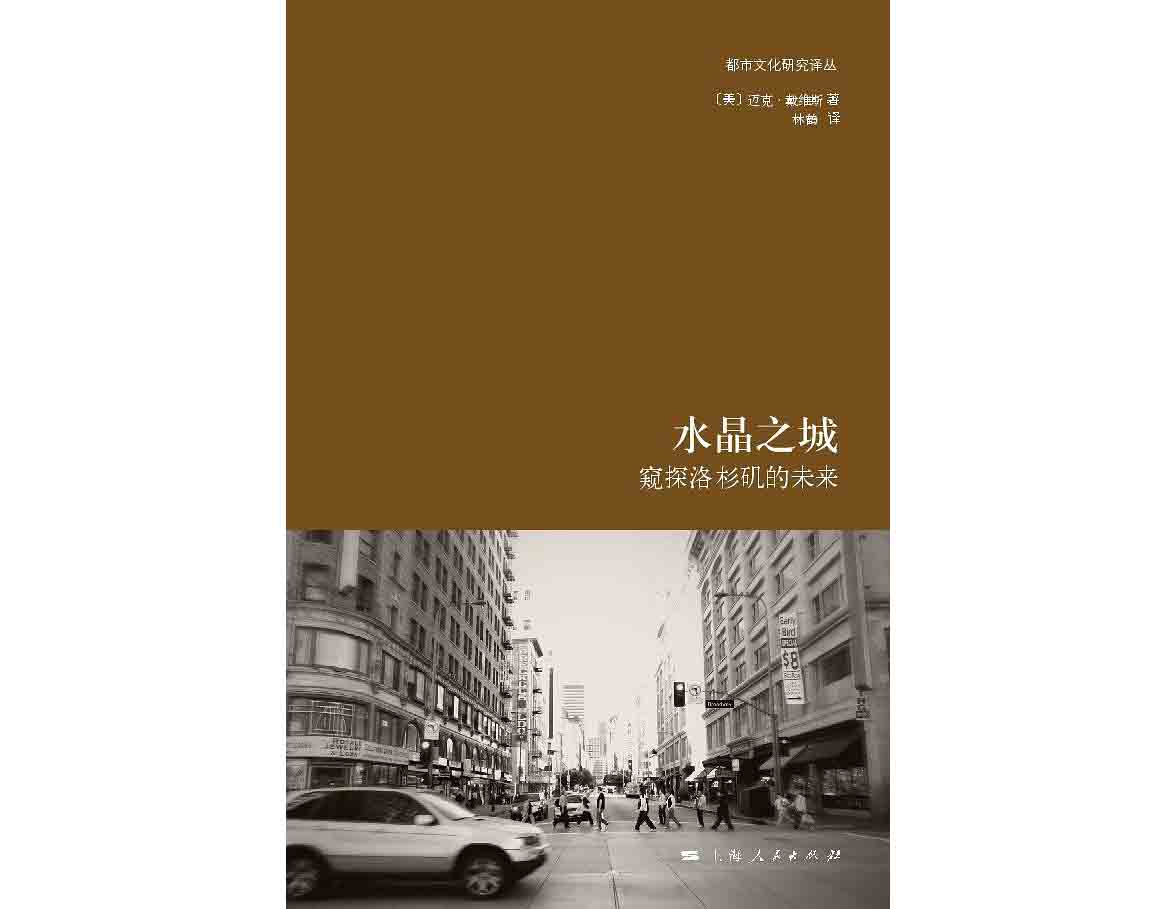
可见,堡垒城市所郑重承诺的安全,不过是岌岌可危的安全。电影《雪国列车》(2013)中,人类近乎灭绝,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登上了威尔福德工业开发的列车(城市的另一种形态),成为永不停歇的流浪者。没有人能够下车,因为滚滚向前的雪国列车之外是万劫不复的极寒深渊。下层阶级挤在肮脏犹如下水道的末端车厢,而上层阶级则在宽敞舒适的头等车厢里寻欢作乐。


《饥饿游戏》(2012,2013,2014,2015)的当权者同样把城市分成了三六九等,并布重兵严防死守,以确保隔离的秩序。命运的不公令人绝望,革命与暴乱终将降临。
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2013)中,以色列筑起高高的城墙以防御僵尸的入侵,但自保的高墙随时有可能变成围困的牢笼。僵尸如山累积、越墙而来,城市猝然沦陷,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要在亲手打造的隔离城市中突围逃生。


(四)虚拟城市:拟象和云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未来城市,其新型的空间形态是「虚拟城市」,以拟象与云端为特征。虚拟城市是信息技术时代的一种新型隔离城市。虚拟城市意味着隔离权力不再诉诸空间赋形,未来城市本身即为一个隔离于现实的幻象。


早在 1975 年,鲍德里亚就富有洞见地指出:拟象在先。鲍德里亚敏锐地发现了一个趋势:由于大规模的类型化,拟象和仿真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在「超现实」之中,面对「真实的沙漠」我们望眼欲穿——绿洲已然绝迹,海市蜃楼却处处可见。
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它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象。
苏贾汲取了鲍德里亚的理论,提出了「拟象城市」的概念。苏贾认为,未来城市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工厂,只需付费即可进入,虚拟城市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环境。
关于虚拟城市的电影情节往往设定如下:大多数人昧于隔离的真相,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城市的异常。主人公不得不求助于混杂势力,设法突出重围。最终,站在世界尽头的主人公幡然醒悟,告别或破坏虚拟的隔离空间。
在丹尼尔•伽洛耶的长篇小说《三重模拟》(1964)中,科学家为了研究市场营销,在计算机环境中建造了一座「虚拟城市」,里面的电子人却对此浑然不觉,只有主人公觉察到了真相。但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三重模拟」——主角最后发现自己以为是现实的世界竟然也是另一个世界的「虚拟现实」。


小说后来由法斯宾德改编为电影《世界旦夕之间》(1973),并由好莱坞翻拍成《异次元骇客》(1999)。此后的《黑客帝国》(1999)、《盗梦空间》(2000)等电影均受其启发。


在《黑客帝国》中,人类惨败于机器人之后,肉身被囚禁,如同电池一般为「矩阵」提供日常所需的能源,反过来,「矩阵」则为人类营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并模拟出人类生活的一切感觉。


如果说「任意浪游」的虚拟城市还太过遥远的话,那么「云端」城市仿佛就在眼前。电影《她》(2013)所描绘的未来城市,诚然是一个温暖的世界:街道干净平稳,室内舒适温馨。设计总监坦言:
我们指望电影是乌托邦的,如果不是,那至少也得是一个舒适的世界,主人公犯不着去跟整个邪恶世界开战。
在未来城市,技术对人的裹挟是如此地全方位,以至于已经没有人愿意跟周围的人聊天了,即便偶尔说上几句也尽是客套和敷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内容干瘪,而且欲望枯竭,大家只愿意跟无比贴心的人工智能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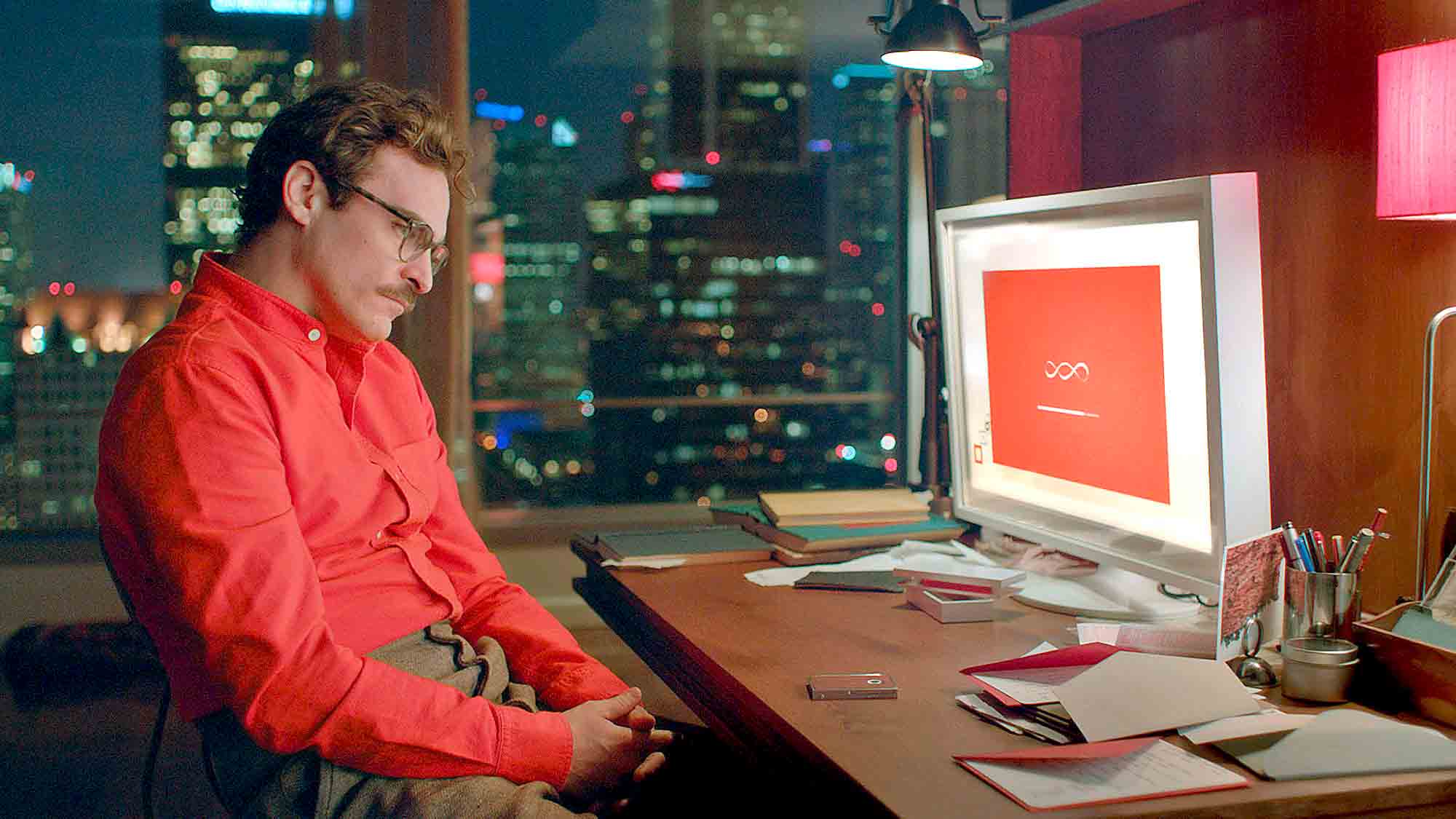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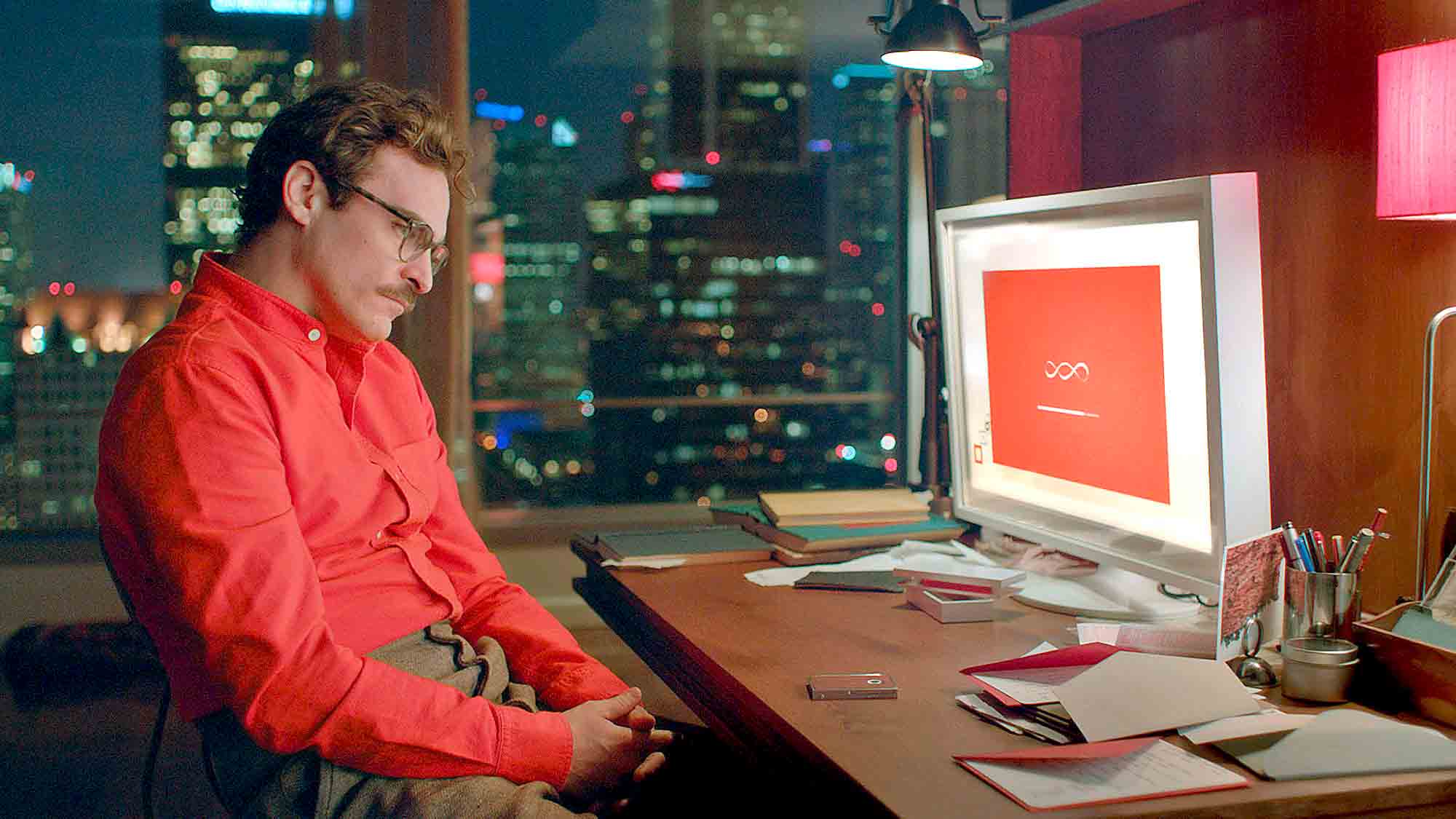
人们处于虚拟城市的甜蜜拥抱之中,但同时也是处于虚拟城市的潜在隔离之下。尽管身处其中的人们会感到有些异样、有些不快,甚至有些慌张,但人们无法拒绝虚拟城市的规定性与隔离性。
威廉•吉布森把未来城市的虚拟化比作「迪斯尼化」,即分派给城市一个特定的主题,主题是规定的、不变的,就好比主题公园一旦落成,其主题就无法重新设定。吉布森强调,自上而下的操控,最终导向的是禁锢而非自由,这是每个封闭式景观的诅咒。


吉见俊哉指出,迪士尼乐园最值得注意的空间特性在于它的封闭性和自我完结性:迪士尼乐园禁止任何俯瞰整个园区的视点存在。
园区来回走动的游客,视线都闭锁在个别城堡与剧场的故事情境中,绝不会散逸到外面。甚至游客还会受邀进入某个情境成为剧中『人物』,一起同乐展演特定的角色。
在虚拟城市中,故事的剧本早已被写就,故事的场景也早已被设定,自行创设故事是被严令禁止的。


二、未来城市的隔离术
隔离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弥漫在未来城市的空间之中,阻隔视听,限制进入,拒绝分享空间的功能。身处其中的人们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有章可循,有迹可查。
更重要的是,隔离主义被合法化、被自然化,或者在暗中悄然施行,未来城市被判定为亟待保护,以免受到异质性力量的侵害。
说到底,隔离的逻辑是现代性的逻辑。现代性扫荡了传统法则,即刻立起了新规矩——空间必须是有序的和理性的。海德格尔指出:
现代技术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再仅仅是『手段』,不再委身『服务』于部分人,而是展示了一个明确的统治秩序,一种明确的规训纪律和征服意识。
这也正是韦伯所谓的「合理性的铁笼」,即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一切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
芒福德也指出了现代都市的尖锐矛盾:城市提供稳定安全的同时,其控制的意图不可遏制,释放与奴役共存,自由与强制并至。未来城市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进入现代性的必然之中,现代性演化至极端便是隔离的执行和扩张。


隔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科幻故事里的未来城市往往糟透了,而隔离主义的首要承诺便是安全。戈尔德考察了 20 世纪以来的科幻电影,发现未来城市往往不甚美妙,多为爆炸骚乱、环境恶化、暴力横行的警告和注脚。
隔离主义的好处是简单清晰,讲理性,有效率——毕竟消除困扰的优先选择便是在空间上做简单的切割,譬如与核尘相隔离的地下城市、与僵尸相隔离的高墙城市。隔离主义的坏处是对复杂的、不清晰的但可能是丰富的事物的取消。简单隔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空间治理者的自负,尽管这种自负很可能是致命的。


隔离之所以得以实现,仰赖于各式各样的空间隔离术。
一方面,隔离术诉诸对流动的阻隔。需要指出的是,这与「种族隔离」不尽相同。种族隔离是一种社会排斥,是对特定种族的歧视,即通过某些方式阻隔个体全面参与社会。而未来城市的空间隔离术是一种阻止流动的极端想象,是空间维度上的切割和隔绝。
另一方面,隔离术也包括对视觉的隔离,至少是对那些不太令人愉快的风景的隔离。垂直城市遮蔽了劳工的苦难,极权城市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堡垒城市遮蔽了穷人的挣扎,而虚拟城市则遮蔽了现实的粗粝。


隔离的手段或许合乎理性,也颇有效率,但很难说隔离是道德的,因为隔离意味着对自由的妨害。隔离为精英们提供了暂时的安全与便利,却也埋下了祸根——疏离感在被隔离者的心中逐渐滋生。倘或隔离毫无休止地扩张,自由力量将挺身抗暴。
基于对 20 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洛杉矶城形象的考察,伊恩•斯科特感叹道,电影里的主人公们「太希望在这座将他们牢牢禁锢的城市的空间界限之外获得新生了」。


三、混杂的进击与退守
一个幽灵,混杂的幽灵,在隔离城市游荡。
一方面,混杂是不受驯服的异域空间,藏身于未来城市的隐秘一隅。混杂空间是隔离空间的反面,是隔离秩序力所不逮、束手无策的地方。混杂之地并不十分美好,往往意味着污秽、粗粝、野蛮、狡猾、法外之徒、名誉败坏、遭人蔑视……以往用于控制这些混乱元素的原则和机制在混杂之地统统失效。
另一方面,混杂是一股势力,是隔离秩序的潜在威胁。混杂拒绝一切的收编与改造,看准时机就大胆进犯,见势不对就仓皇退守。混杂之地是反抗势力酝酿进击和最终撤退的地方。


苏贾认为,尽管后现代城市的某些中心已经瓦解了,但中心依然是中心,其向心力依旧发挥作用。然而,监控并不总是奏效,注定有监控鞭长莫及的地方,因此,城市各处始终留有抵抗、拒斥和重新调整方向的余地,由此滋生出一种积极的空间性政治。
混杂是隔离的产物,也是隔离的掘墓人。
隔离总是试图将混杂排除在外,进而一手塑造了混杂地带。隔离空间拒绝流动,至少让原本合法的流动看上去没什么指望了。纯洁性与统一性的铁幕落下来了,而混杂是遏制隔离扩张的最后希望。空间内为数众多的被排斥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无以应对隔离的坚硬壁垒,唯有祭出混杂大法。
混杂势力热衷于破坏隔离空间,以此实现对权力的反叛。他们抹除其边界,猛攻其堡垒,破坏其稳定,嘲弄其刻板,打破其惯例,骚扰其执法者……总有人想在这权力的标记上乱涂乱画,推倒它,碾碎它,焚毁它,甚至用排泄物玷污它,从而创造出新的象征意义。


未来城市常常被封闭在一个巨大的人工穹顶之内,与城市之外的自由荒野形成鲜明对比。幽闭是压迫与恐惧的源头,而旷野则意味着舒适与自由。
电影里的主人公为了争取自由而奋起抗争,试图从禁闭之中逃脱出来,于是一路砍砍杀杀,奔向隔离势力鞭长莫及的旷野。
未来城市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受制的城市,禁闭的城市,以及废墟的城市。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性的分类光谱:
某种威胁自由的压迫性力量渐次滋长,最终禁锢全城;
与此同时,维护自由的反抗性力量也在增长;
最后,两股势力展开终极对决,而城市则要付出沦为废墟的代价。
未来城市犹如坐在火药桶之上,随时可能会遭受致命一击。
混杂之地的最大价值就是保存了自由的火种。尽管这种自由往往显得过于另类,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但混杂之地毕竟为另类的选择提供了庇护。隔离空间的觉醒者的头顶上是一片不断被吞噬的天空,反叛者至少可以像幽灵一样从隔离空间侧身逃走。
尽管避入混杂有时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混杂之地让我们有机会审视异己之物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混杂之地能够提供久违的真相,提供喘息的间歇,提供潜在的援军,提供逃逸的希望。


然而,混杂有时是可怖的。隔离的被打破,意味着极端的冲突、秩序的颠覆,甚至全盘毁灭。尼采有言: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混杂以极端相反的逻辑去反抗隔离:用肮脏来对抗纯净,用混乱来对抗齐整,用游击来对抗堡垒。尽管混杂最终胜利了,却埋下了矫枉过正、甚至是失控的祸根。混杂势力破坏起来雷厉风行,围墙崩坏,防范溃败,新的秩序却无从建立,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安全。
电影《大都会》(1927)警告我们:倘或劳工胆敢进犯,机器必将应声崩塌,最先遭殃的是底层劳工的子女,他们随时有可能被不断上涨的洪水淹死。
不过,混杂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提醒空间统治者强制隔离所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秩序可能在一夜之间猝然消失。


结语
空间即政治,这同样适用于未来城市。空间是可供摆放的支架,权力藉此施展开来;空间也是上下隔离的支架,服务于等级秩序。未来城市的空间治理术是制造隔离以免于冲突,其假设是:
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极化与混乱,而隔离是确保秩序得以维持的必要手段。为了应对特定的社会危机,隔离的城墙拔地而起,耸然矗立。
隔离意味着自由的受限,混杂意味着流动的可能。隔离之地将多样性驱逐殆尽,而混杂之地则是多样性的容身之所。混杂蕴含的反抗性对隔离空间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混杂势力是打破隔离、赢得自由的希望所系,不过隔离秩序的崩坏往往代价惨痛。
身处未来城市的主人公的首要使命是逃离抑或打破隔离。唯有取道混杂之地、假手混杂势力,藉此反抗隔离,方能彰显正义。


不过混杂势力终究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除了自由之外别无理念,亦没有提供一种新的规划或设计。未来城市试图让我们相信:隔离是危险的,设计是可耻的,或者说设计本身必然会导向某种罪恶;
唯有拒绝规训、打破隔离,正义才能得以伸张。
「混杂势力对抗隔离空间」的「未来叙事」体现了西方科幻电影的激进政治传统,这也是未来城市的空间政治的真正浮现。


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责任编辑 胡一峰,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8年第8期全文转载,第37-46页

